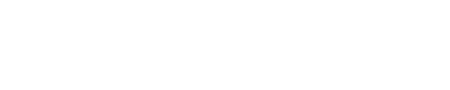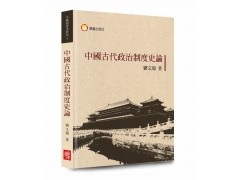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論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論-出版內容簡介
本書的緒論和代跋十分精彩,有諸多創見。皇帝制度板塊梳理出帝制誕生演變發展消亡的軌跡,分析了人與法的互動及其對帝制的不同影響。中央政府板塊詳述了從三公九卿制到三省六部制再到內閣軍機制的變化,論證了中外朝兩套班子併行、監察對政務控制、層級與垂直交錯的中國特色之歷史淵源。地方體制板塊勾勒出從分封制到郡縣制再到行省制的演變線索,揭示了巡迴監察與親民行政之間的關係,基層官員與吏胥幕隨的不同。官僚制度板塊羅列出不同朝代選拔培養任用考覈俸祿待遇的制度組合,對察舉辟除和科舉等制度的作用機制進行了深層剖析。 #蘭臺出版社#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論-作者介紹
劉文瑞
西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主要從事管理思想史、文化史、中國政治制度史和管理理論等方面的研究。主要著作有:獨著《繼承與變革——中國古代人事制度的發展歷程》、《唐玄宗評傳》、《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歷史深處的管理智慧》、《管理學在中國》、《邊緣瑣語:人文與管理的對話》、《史海管窺:掌故中的管理智慧》、《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史論》等。合著《中國古代廉政制度史》、《管理社會的杠杆——當代西方公務員制度》、《管理思想大系》等。參與編寫了張豈之主編的《中國思想史》、《中國思想文化史》、《中國歷史十五講》;余華青主編的《中國廉政制度史論》等。曾發表學術論文70餘篇,各種評論、隨筆、普及文章500餘篇,涉獵領域包括歷史學、政治學、管理學等學科。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論-序
緒論 中國政治制度史綱要
中國政治制度史是一個寬廣的學術領域,然而,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卻存在一定問題。儘管有關中國政治制度史的文章著作極為豐富,但數量上的琳琅滿目掩蓋了品質上的內在缺陷。粗粗看去,研究成果越出越多,使人目不暇接;細細想來,極少有新著能夠回味咀嚼。浩瀚的史料堆砌之後是理論的蒼白,雜亂的典章拼湊之間是邏輯的混亂。回歸文本,仔細梳理制度的演變脈絡及其運作機制,方有可能為研究中國政治制度的歷史變遷提供一個學理體系。
#蘭臺出版社#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論-目錄
目錄
緒論 中國政治制度史綱要 1
一、中國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對象、內容、重點及有關問題 1
二、中國政治制度史的發展線索和基本趨勢 7
三、中國政治制度史的基本特點 18
第一編 皇帝制度論 25
一、先秦時期的早期君主制度 25
二、皇帝制度的誕生——秦漢帝制 42
三、皇帝制度的「青春期」——魏晉南北朝帝制 55
四、皇帝制度的發展——隋唐帝制 58
五、皇帝制度的「更年期」——宋元帝制 70
六、皇帝制度的爛熟和回光反照——明清帝制 78
第二編 中央政府論 113
一、中央政府的初級形態——先秦 113
二、專制一統集權王朝的創建——秦漢的中央政府 119
三、動盪過渡時期的調整——魏晉南北朝的中央政府 142
四、新的大一統政權——隋唐的中央政府 166
五、王權的強化和異化——宋元的中央政府 218
六、傳統政權的極致——明清的中央政府 247
第三編 地方體制論 299
一、從部族國家到疆域國家——先秦分封制與郡縣制 299
二、監控與治民的協調——秦漢的地方體制 303
三、建制調整——魏晉南北朝的地方體制 326
四、多樣化與地方勢力的消長——隋唐的地方體制 330
五、監控的強化和親民的弱化——宋元的地方體制 345
六、建制演變與吏治危機——明清的地方體制 353
第四編 官僚制度論 393
一、從貴族向官僚的演變——先秦官制 393
二、早期官僚系統——秦漢官制 411
三、在迂迴中前進——魏晉南北朝官制 451
四、官僚系統的創新和體系化——隋唐官制 464
五、官僚系統的完善和變異——宋元官制 511
六、官本位的高峰——明清官制 556
從歷史中汲取治國理政的智慧(代跋) 606
一、傳統史學的本質 606
二、汲取歷史智慧的層次 610
三、傳統史學對治國理政的啟迪路徑 616
正體版後記 623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論-內容連載
第一編 皇帝制度論
一、先秦時期的早期君主制度
廣義上的先秦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由無階級社會向階級社會的過渡時期。這一時期,中國歷史上的君主制度從無到有,從而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這一時期的君主,其產生、繼承和更替的方式和制度,雖然有著發展階段的不同,但卻具有一個共同特徵,就是一直保留了濃厚的原始色彩。
(ㄧ)原始社會人類首領的產生方式及制度規範
如果我們以公共權力的有無作為標準來界定政治,那麼,原始社會同樣有政治。如果我們以階級鬥爭的有無作為標準來界定政治,則原始社會不存在政治。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顯然前一種界定較為合理。
大量的考古資料表明,中國早在六七千年以前,就有了豐富多樣的新石器文化,而且已經有了完善的氏族組織和部落組織,自然也就隨之有了較為穩定的首領產生方式。
人類一旦有了組織,就必然要有首領,這就同樂隊要有指揮的道理一樣簡單。據理推之,恐怕在藍田人、北京人時期,人類就存在著首領。這一點雖然在目前尚無資料證實,但從人類的近親——靈長類動物來看,首領是確實存在的。在黑猩猩、大猩猩等動物的自然群體裡,那些靠勇猛、靠膂力、或者還要靠一點聰明而取得首領位置的佼佼者,規定著群體內的等級和秩序,脅迫其臣民按牠們的意志行動。
人類和動物不同的地方,在於人類有思維,有語言,能夠以協定、契約的形式來達成動物界必須以角力和征服才能達成的目標。但是,人類的思維、語言能力也是隨著人類自身的發展才發展起來的。藍田人的腦容量僅有782毫升,比現代人的1430毫升幾乎相差一半。因此,我們絕不能夠拿現代人的思維水準來推斷原始人的協商和契約能力,原始人也絕不可能有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制度。用現代人的觀點去推論古代的實際情況,是歷史研究中經常出現的失誤。特別是關於民主問題,如果用現代人類對民主的認識來理解原始社會的民主狀況,就有可能對古代的民主產生極大的曲解。由此來看,人類最早的首領,幾乎可以斷言不能也不會以民主推選的方式產生。以靈長類動物來推論,最早的人類首領,只能是靠武力、靠征服、靠血淋淋的爭奪產生。
問題在於,當人類進入了新石器時代,有了氏族與部落這樣的血緣組織之後,首領的產生是否還需要武力?要弄清這個問題,又必須弄清它的前提,即氏族與部落的首領由誰來擔任?
傳統觀點認為,人類最先進入母系社會,再進入父系社會。在母系社會裡,由德高望重的婦女擔任首領;在父系社會裡,由男性推選首領。現在看來,這種說法不確。
首先,母系社會和父系社會的前後關係是否構成社會發展的必然序列就大有疑問。大量的人類學、民族學、考古學資料證明,人類歷史上確實存在過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但母系與父系之間不存在必然的前後繼承關係。我國已經有人對仰韶文化母系社會說提出了質疑。而且就在仰韶文化時期發現有父系社會的遺址。
現代西非的調查資料也說明,處在同一發展水準的部落中,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是併存的。因此,母系社會和父系社會的劃分,並不一定是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劃分。再進一步說,人類歷史上有母系氏族,但母系社會並不一定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有的學者甚至斷言,在人類的歷史上,並不存在一個必然由婦女擔任首領的、非經不可的歷史階段。
其次,即使人類社會必須經歷一個母系社會階段,也不一定由婦女掌握公共權力。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的區分,是社會組織結構的區分而不是掌握權力者性別的區分。在很多母系氏族中,婦女雖然受到尊重,在社會生活的某些領域具有一定的權力,但在經濟、宗教、軍事等領域中的真正權力卻歸於男性掌握,特別是那些「母親」的年齡最大的兄弟,具有掌握權力的優先地位。如印度馬拉巴爾海岸(Malabar Coast)的納亞爾(Nayar)人、特羅布里恩島上的土著居民、北美的納瓦霍(Navaho)印地安人,以及加納的阿散蒂(Ashanti)人,都是母系氏族而由男人掌權。那種認為女性在社會生活、特別是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佔主要地位,就必然要由婦女掌權的推斷,在邏輯上是無法成立的。我國雲南德宏的傣族,婦女擔負全部生產勞動的三分之二工時,但其社會地位卻十分低下。上溯五百年,「其俗賤婦人,貴男子,耕織徭役擔負之類,雖老婦亦不得少休」。這種現象絕不是個別的,相反,在母系氏族中婦女生產、男子掌權的現象卻是較為普遍的。
據此推斷,歷史上的人類首領,即使是在母系社會存在的情況下,也可能是一直由男人充任的。
那麼,這些由男人充任的首領又是怎麼推選出來的呢?
從人類近親靈長類動物的情況來分析,可以肯定地說,人類首領的產生必然存在一個暴力爭奪階段。但是,隨著人類智力水準的提高,或遲或早,人類總會認識到,靠殺戮方式在同一群體內部爭奪首領地位的方式會削弱群體力量,是不明智的。經過漫長的發展,人們終於發現了可以用和平推選或自然繼承的辦法來產生自己的首領。這一漫長的過渡,從歷史資料來推論,大約從舊石器時代延續到了新石器時代的初期。當代民族學調查的資料證明,母系社會也好,父系社會也好,均已基本排除了以暴力爭奪首領位置的方式(當然,在個別情況下,尤其是在現有首領軟弱無力的情況下,人類仍然易於回歸到以暴力奪取首領位置的方式。但是,這只能說是一種復古,而不能說是進化)。母系氏族中多由母親年齡最大的兄弟掌權這一事實證明,在母系社會,首領產生的方式以血緣遠近為主要依據,在此基礎上可進行適當選擇,一般選經驗豐富者或具有宗教地位者。這種選擇並不是按我們所想像的方式民主推選,而是一種按慣例進行的血緣繼承。只不過這種繼承要取得同氏族成員特別是氏族貴族的認可而已。如果同氏族成員不認可,則輔之以武力的或非武力的競爭。
根據文獻資料和民族學資料來看,在父系社會,由於繼嗣的明朗化,首領的產生基本上採用血統繼承方式。也就是說,在父系社會,廣義上的「父傳子」繼位方式已經確立。那種把父傳子、兄傳弟繼承方式作為國家產生標誌的觀點,忽視了原始社會的社會組織形式以血緣關係為基本紐帶這一特徵,缺乏科學的立論依據。國家的產生,特別是中國歷史上國家的產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找出一個明確斷限的努力,在一定意義上是不可取的。我國史學界長期把夏禹傳位於啓作為中國歷史上國家誕生的標誌,其實是把理論教條化、把科學研究形而上學化、把歷史資料剪裁得適用於自己觀點而帶來的謬誤。
就拿文獻有明確記載的先商、先周世系來說,本身就否定了父子相傳是階級社會標誌的論點。按《史記.殷本紀》所載,校以卜辭,商族自簡狄「吞食玄鳥之卵」而生契,直至成湯代夏,父子相傳凡14代(根據卜辭補入王恒,實為15代),如下所示: (1)契。(2)昭明。(3)相土。(4)昌若。(5)曹圉。(6)冥。(7)王亥(一作核,《史記》誤作振)。(8)王恒(《史記》無)。(9)(上甲)微。(10)報丁。(11)報乙。(12)報丙。(13)主壬。(14)主癸。(15)天乙(湯)。 按《史記.周本紀》所載,周自姜原「履大人足」生棄後,直至武王代商,父子相傳凡16代,如下所示: (1)棄(后稷)。(2)不窋。(3)鞠。(4)公劉。(5)慶節。(6)皇僕。(7)差弗。(8)毀隃。(9)公非。(10)高圉。(11)亞圉。(12)公叔祖類。(13)古公亶父(太王)。(14)季歷(公季、王季)。(15)昌(西伯、文王)。(16)發(武王)。
很明顯,先商和先周起碼有相當長時期處在氏族社會階段。我國史學界的研究中,對先商與先周的氏族社會何時解體、何時進入階級社會雖然有不同意見,但公認為商在第七代王亥以前,周在第四代公劉以前,無疑還處在氏族社會階段。用血緣繼承關係作為進入階級社會的標誌,無法對先商和先周的歷史作出合理的解釋。
如果再向前推,《史記》還排列了上古的世系繼承關係。依照《史記》的說法,上古的「人文始祖」黃帝與堯、舜、禹之間,黃帝與夏商周三代的祖先之間,都具有血統繼承關係。假若《史記》的說法能夠成立,我們以夏禹傳位於啟作為進入階級社會標誌的論點進行邏輯推演,則不僅從夏商周的始祖,而且上至堯舜禹乃至黃帝時期就早已進入了階級社會,豈不荒謬!當然,《史記》的記載尚有許多疑問,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既然父系社會就有了原始的繼承制,那麼,在邏輯上就應有了以繼承制產生首領的方式,而且很有可能以繼承制產生首領的方式為主。結合有關禪讓制的傳說來推斷,在父系社會裡,首領一般由繼承產生,但如果按繼承方式即將接替首領位置的人選不勝任,也就是在對繼承者有較大的不同意見的情況下,則可用推選方式作為繼承方式的補充和替代。而階級社會的王位繼承制,與原始繼承制的不同之處,只不過是不再「諮之四嶽」,即不用再取得共同認可,而且可以用暴力鎮壓不服者而已。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歸納出,原始社會是人類剛剛從野獸狀態脫離出來的階段,是人類文明最不發達的階段。最早的人類首領產生方式,肯定帶有動物界弱肉強食的痕跡,後來才緩慢地走上了和平道路。而這種和平乃是求生的必要手段,是被迫的、愚昧的,絕不能把它美化為現代人所崇尚的自由平等。民族學和人類學的資料證明,部落社會、氏族社會也存在著差別和不平等,部落或氏族的成員在性別之間、年齡級別之間、某一特定集團與其他集團之間,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權利和權力的不平等。因此,人類擺脫了動物界那種血淋淋的產生首領的方式後,所形成的首領產生方式,並不像有的人想像的那樣,是平等的推選方式,而只能是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繼承方式。雖然母系社會與父系社會的血緣繼承方式在計算血統上的標準不同,但卻不可能擺脫這種方式。民主推選首領,充其量是對血緣繼承方式的認可辦法或者是修正辦法,不可能成為原始社會中首領產生方式的主體。對上古民主制度的推崇,一半是事實的誇大,一半是後人的美化。李宗桐先生在《中國古代社會史》中曾指出:「堯舜禪讓尚能以另一個假設解釋……即王位似由舅甥以傳。」如果以甥舅相傳解釋禪讓制,則會使禪讓制代表古代民主的觀點不攻自破。
必須指出的是,部落聯盟的首領產生方式在原始社會中不具有代表地位。部落聯盟首領的產生,多半是靠部落之間的實力對比。而且,部落聯盟是否為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進化的必經階段,也是一個大有可疑之處的問題。摩爾根當年把部落聯盟看作是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發展的必然階段,只是看到了易洛魁社會中存在著部落聯盟而得出的推論,有一定的局限。在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中,部落聯盟並不常見。特別是把中國歷史上的炎黃時期看作部落聯盟時期,實際上是把摩爾根模式硬套過來的結果,並不十分可靠。因此,部落聯盟的首領產生方式,可以視為父系氏族或部落首領產生方式的一種特例,在現有資料的基礎上,尚不能把它作為由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的普遍形態,更不能把它作為社會發展的一種基本規律。
原始社會的人類首領,如氏族首領、部落酋長、部落聯盟的軍事長官,都具有其相應的權力。歸納起來,這種權力大致有以下方面:
(1)宣戰媾和權。對於外氏族、外部落與本氏族、本部落之間的衝突,氏族部落首領有權決定戰和問題。
(2)生殺予奪權。對外族成員侵犯本族,氏族首領有權代表本族對其施加一切處罰。對本族成員有違反族規(如習慣、禁忌之類)者,或本族成員有不利於本族公共利益的行為者,氏族首領有權依照慣例對其施加族內處罰。這種對族內成員的處罰一般有三種方式,即:全部或部分剝奪個人生活資料、驅逐出本族之外(即後代所謂的流放)、處死。同時,氏族首領還要裁決族內糾紛。
(3)領導權。主要是組織領導本族的生產活動。
(4)宗教權。氏族首領在宗教上的權力一般較小,通常情況下,氏族中的宗教權是由氏族首領以下的宗教成員(巫、祝之類)所掌握。這些宗教成員代神發言,對於氏族首領形成一定的制約。多數情況下,執掌宗教權力的巫祝要和執掌世俗權力的首領互相配合,達成一定程度的溝通,共同處理氏族公共事務,行使統治權。
現代民族學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調查資料,為我們瞭解氏族首領的權力提供了方便。如大洋洲西新幾內亞的達尼部落德洛摩-馬貝爾氏族的酋長庫魯路,在鼻子的中隔上穿了個洞,用來戴豬獠牙,以作為他擁有權力的標記。在南太平洋的新赫布里底群島南巴人的部落,伊拉南賓平酋長以氣派的服飾表示其酋長地位。在墨西哥南部瑪雅文化博納柏克遺址的一座建築物上有一組壁畫,其中的酋長與別人不同,他戴有頭盔,上衣、腳鐲和長矛都用美洲虎皮包著,這是他崇高地位的象徵。在大洋洲新赫里多尼亞諸島上,首領的標誌是住在高頂圓形茅屋裡,茅屋的頂尖上有象徵性的雕刻,此外,首領還擁有儀仗斧以及傳統的貝殼幣等等。在拉丁美洲復活節島上,部落首領執有權杖,權杖的頭上為一雕刻後塗彩的人面像。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酋長要比其他人富裕一點,並佔有較大的席帳,他的標誌是穿一件豹皮或山貓皮的長袍。等等。我國許多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出土有大量的權力象徵物。這些出土文物的主要類型是象徵戰爭和生殺權的斧鉞,商代早期甲骨文中的王字作(金文為「」),到祖甲起變為(金文為「」),學界多解釋為斧鉞的象形字。其次還有象徵宗教權的玉璧、玉琮等物。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原始君主的地位,一般通過其居住、服飾的不同來加以象徵。他們都具有本族成員必須服從的地位,本族成員對其首領,一般都有一種十分尊敬的卑下感。他們對其首領的尊敬和服從,主要是依據習慣。這些氏族首領一般都不脫離社會生產以及其他氏族活動,特別是遇到對外族的戰爭,氏族首領必須親自領導並參加作戰。
原始社會氏族、部落首領以及部落聯盟首領,其行為主要依據本氏族或本部落的習慣規範。他們要嚴格地按照自己族內的傳統和慣例辦事。如果他們違反了傳統慣例,就會產生兩種情況,或者是他們的行為能夠取得氏族成員的認可,在本氏族中形成新的習慣;或者是在氏族成員的反對下被放逐,氏族另外產生出新的首領,或以原先確定的繼承者取而代之。
(二)國家誕生後的早期君主產生方式及制度規範
伴隨著國家的產生,原始社會的首領,變成了階級社會的君主。而什麼是國家?國家是怎樣起源的?至今仍有許多爭論。在國家起源問題上,代表性的著作有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傅禮德(Morton H.Fried)的《政治社會的進化》(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an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佘威士(Elman R.Service)的《國家和文明的起源》(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5)等。大體上,現代學者普遍認為,國家產生的必要條件有兩個:一是以地域關係取代血緣關係,二是要有合法的武力。第一個條件的表現形式是統治者有了領土主權,其社會成員的居住基於職業分工而非基於血緣或姻緣關係,有了集權的中央政府。第二個條件的表現形式是國家獨佔武力,有了法律,在原始社會時由被侵犯者及其親屬以復仇方式掌握的罪行懲罰權轉移到了國家手裡。最集中的概括起來,就是國家必須要有一個凌駕於社會之上的統治集團,必須有自己的疆域。
中國古代的夏商周三代,大體上就是中國歷史上的早期國家時期。按照張光直先生的判斷,三代與其說是先後遞進關係,還不如說是列國併存關係。在大體方位上,周人在西,夏人在中,商人在東,地理上重疊較少;三代都實行城邑式的宗族統治,夏為姒姓,商為子姓,周為姬姓,姓各不同,但以族姓治天下則是一樣的。張光直先生認為,三代的前後相繼,實際是在同一歷史時期內,三國之間勢力強弱的沉浮而已。本書取張光直先生之說,把夏、商、周的君主制度視為一個制度體系。事實上,三代的君主制度,雖然前後有所損益,但總體看來,相因者居多。直到周室東遷,才發生了較大變化。
夏代世系,據《竹書紀年》記載,從禹至桀共 14 代 17 王,歷時 471 年(《漢書》引《帝系》云 432 年,《初學記》引《帝王世紀》亦云 432 年)。商代世系,據《史記·殷本紀》記載,凡傳 17 代 31 王,歷時 496 年(《竹書紀年》曰 496 年,《三統曆》曰 629 年)。其世系在甲骨卜辭中得到了證實。西周世系的資料較多,凡傳11代12王,線索清楚。
關於三代的王位繼承方式,我國史學界的基本說法是:夏人父死子繼,商人兄終弟及,周人又父子相傳。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即三代君主的產生方式是繼承制而非選舉制。還有一點也是肯定的,即夏商周三代,特別是商周二代,在取得國家統治權以前與奪取國家政權以後,其繼承方式大體上是一樣的(僅在夏禹傳位於啓這一點上,我國史學界把它看作一個劃時代的變化。不過,把夏禹傳位於啓作為國家誕生的標誌很難成立,因為以傳子制作為國家誕生的標誌,就無法解釋早商和早周在進入階級社會之前的繼承制度)。需要弄清楚的是,三代的父子相傳與兄終弟及二者之間是怎麼變化的。解開這一奧秘的關鍵,在於昭穆制度。
昭穆之稱,散見於《詩》、《書》、《左傳》等典籍之中。昭穆顯然是西周才有了的定稱,殷商甲骨中未見過昭穆一詞。但究其制度實質,昭穆的含義,卻貫穿於三代始終。
何為昭穆?《周禮.春官.小宗伯》曰:「辨廟祧之昭穆」。《正義》曰:「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周代的昭穆,按文獻所示,是以太王穆、王季昭、文王穆、武王昭的方式排列。而排列昭穆的目的,又是為了確認繼承順序。「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禮記.祭統》)非得排列昭穆,不能明確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說明了此時的繼承制絕不是祖父子孫一脈相承的直系,否則,排列昭穆就沒有意義。因此,只有弄清昭穆制度的含義,才能弄清西周王朝,進而弄清三代君主的產生制度。
現代研究昭穆者,多認為昭穆制度代表婚級。如果以婚級制度來解釋昭穆制度,則三代君主產生制度的有關問題,就能展示出明確的線索。
夏代世系中,已經有了以天干紀世系的痕跡。《尚書.益稷》中,禹有一段話:「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這一段話的關鍵是「辛壬癸甲」四字。據張光直釋,禹是自述他自己的行為比起丹朱來如何正派,如何努力,丹朱朋淫於家,而禹娶於塗山是名門正戶,適當的配偶,是「辛娶壬」、「癸娶甲」之類,同《詩經.陳風.衡門》所謂的「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取妻,必宋之子?」語氣相似,也同西周姬姓娶妻於姜、子、姞相似。《左傳》宣公三年石癸曰:「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商代妣配,商王只有一癸(示癸)其妣果為妣甲,商王共有四辛(祖辛、小辛、廩辛、帝辛),從二辛祀典上看到的王妃名稱,只有直系的祖辛有配,其妣有三:妣甲、妣庚、妣壬,壬為辛之配偶。由此可以推斷,夏商婚配相同,癸娶甲,辛娶壬。從夏世系中所示天干來看,據楊君實《康庚與夏諱》一文曰,康為庚,寧為丁,則啓以後夏世系中以天干為名者出現世次如下:
庚—□—庚—丁—□—□—□—□—甲—□—□—癸
商代的世系隔代相同。如果將夏代諸王列為甲庚同組,丁癸同組,則夏與商的繼承制相同。進一步考察湯(天乙)滅桀(癸),則夏商的銜接點也表現出了隔代世系相同的特點。所以,有人甚至大膽推測預言道:夏商二代,亦或為一。
商代的君主繼承制度,同婚級制度聯繫起來看,如果把商王室看作交表內婚制,則很容易找出其中的繼承關係。商代均以天干紀廟號。張光直先生將商王廟號分為兩組:A組為甲、乙、戊、己,B組為丙、丁、壬、癸。庚、辛則存疑,或列入第三組。則可發現,商王凡兄終弟及者或祖孫相繼者均在同組,而凡父子相繼者均在異組。也就是說,商代的王位繼承制度,具有隔代相同性。由此也反映出,商代王位的產生,是按姻親和血親關係繼承的。
總之,夏商周三代的君主,都是產生於「父死子繼」這一繼統法則。不過這裡的「父」與「子」是指等級輩份,而非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下的父子。「兄終弟及」是父代和子代班輩繼承制度的一種補充。搞不清這一點,就無法理解兄終弟及的來龍去脈及其歷史作用。關於歷史學界對三代繼承制在研究中的誤解,張光直在〈從商周青銅器談文明與國家的起源〉一文中講得十分透徹。他說:
在任何一個學科尤其是歷史很悠久的學科裡面,我們的思想包袱是沉重的。所以有時候,我們要把過去所有的成見暫時地、完全的拋除,從頭想起。以殷商的王權繼承制的研究為例,多少年來,我們所瞭解的就是父死子繼,兄終弟及,這樣一代代地傳下來。我們常常不自覺地毫無疑問地認為:頭一個王是第二個王的父親,第二個王是第三個王的父親。我們之所以會不自覺地作這樣的假定,是因為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許多朝代的帝王繼承傳統就是如此。但是,假如把這個成見拋開,假如從零出發,那麼,我們就沒有理由說,第一代和第二代非是父子關係不可了。問題的關鍵在於父親是不是生父?兒子是不是親子?我們是學習人類學的,知道在很多原始民族裡,有所謂分類式的親屬稱謂,即凡是父輩的都稱父,兒輩的都稱子。在中國的古代,也有這種稱謂,即所謂「伯父」「叔父」都稱為父。如果王乙是王甲的子,王甲便是王乙的父這當然不錯,但是,王甲是否一定是王乙的生父,這就很難說了,或許只是他的伯父、姑父、舅父?關於這一點,從前提上是不能解決的。因為不能僅憑文獻上說是父便一定是生父。我們所要做的是找出種種資料來證明他是生父還是伯父、叔父、姑父、舅父。反之,他的子也不一定就是他的親生子,也許只是他的侄子或外甥(這些稱謂是後來才有的,在商代,只有父和子這兩個稱謂)。實際上,在古代,所謂父死子繼,只不過是表明你這一家的父輩做了王,子(或侄)輩得到王位繼承權的便利就遠比別人多。一方面這種統治別人的權力常跟親屬有關,另一方面要獲得這種權力還要靠王位繼承人本身的本領或道德表現。
問題在於,父死子繼的輩份繼承,繼嗣者往往不止一人,即使無繼嗣者或者繼嗣者不勝任,用兄終弟及的辦法來補救,有資格者也往往不止一人。因此,解決繼統糾紛,乃是殷商統治者的要務。據歷史資料推測,在夏代和商代初期,由於有資格繼承王位的人數比較多,所以極易引起父子兄弟之間的爭奪殺弑。到商末,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產生了嫡庶制。周代則在商末的嫡庶制上發展起了宗法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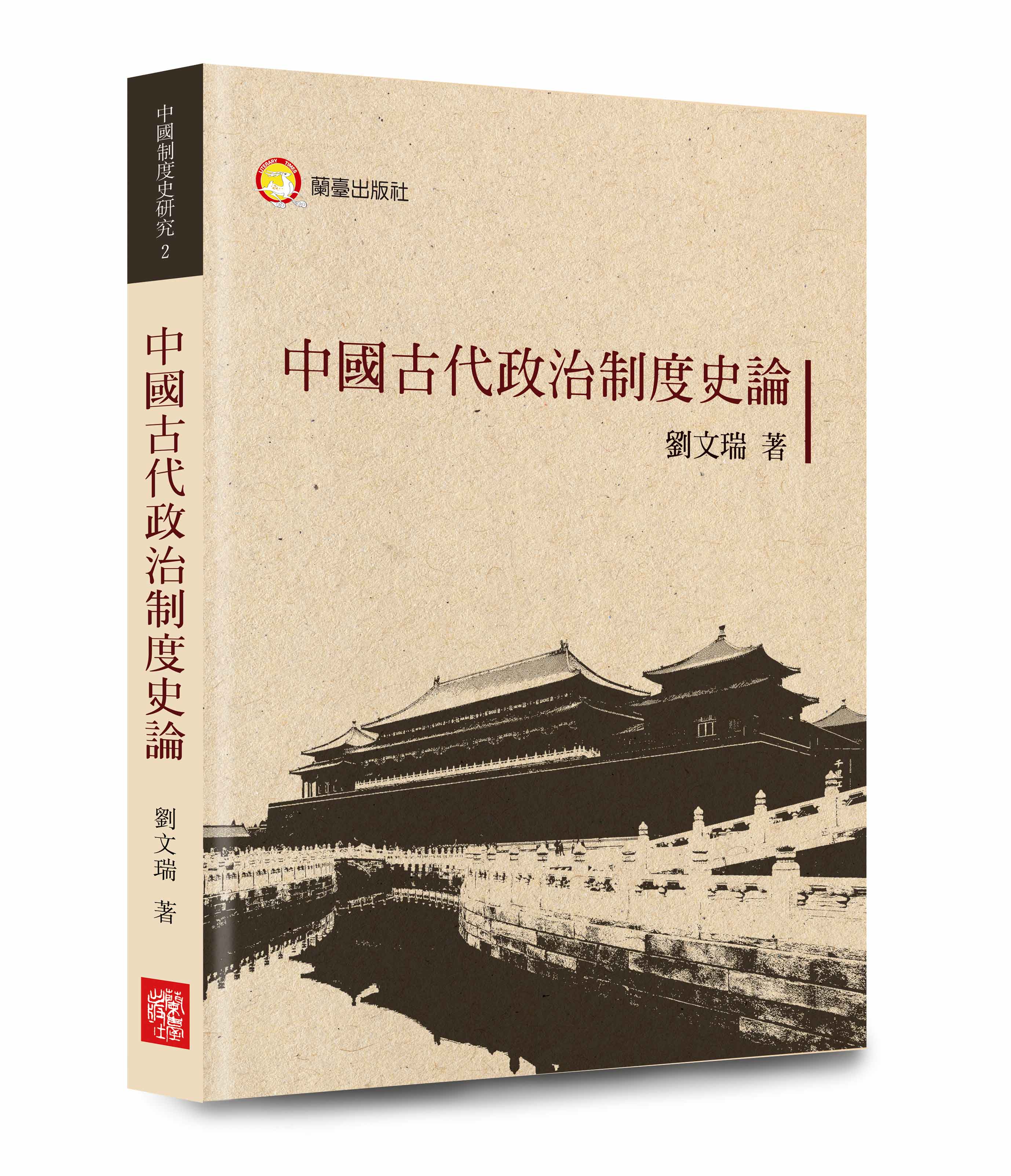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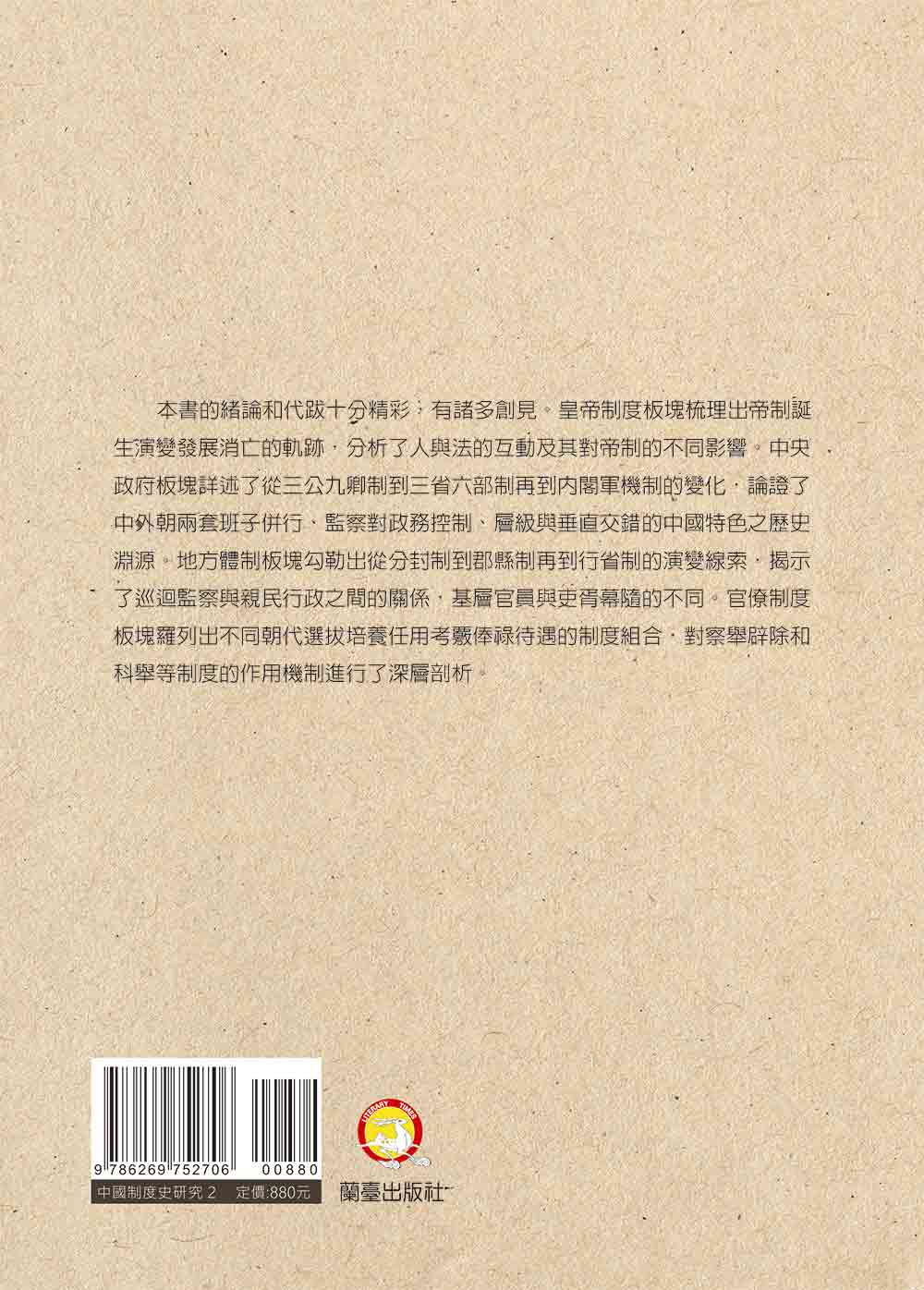
購書注意事項:
一、單筆購物2000元以下,運費100元;單筆購物2000元以上免運費。
二、為了保障您的權益,若您發現購買的書籍有瑕疵,麻煩請您留言或是電話詢問後續處理方式。
三、商品換貨時,麻煩請您留下購買書籍的郵戳或是收據做為憑據。
四、若需要團體訂購,我們有專人服務。來電請洽博客思出版社:
電話:02-2331-1675
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08:30~18:00